石木间有故事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毛泽东的这首《七律・登庐山》很是著名,说起来,与吴宗慈的《庐山志》颇有渊源。
1959年7月,毛泽东初登庐山的第二天,他对地方接待人员讲了个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的是朱熹初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甫一下轿,就开口问迎接他的当地官员是否带来《南康郡志》,迫切地想通过方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治下的人文风土。讲了这个典故,毛泽东微笑着“问志书”――要求看《庐山志》。当时的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林敏立即派人到庐山图书馆找来吴宗慈的《庐山志》。在仔细研读《庐山志》并写下大量批注后,毛泽东乘兴铺纸研墨,一挥而就这首《七律・登庐山》。后来,他又要求再送吴氏的《庐山续志稿》。时隔两年的1961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美庐别墅中留影,影像中他捧在手上凝神细读的,依然是吴氏的《庐山志》。有趣的是,同一年周恩来在庐山观音桥有一帧留影,也手持一本吴氏的《庐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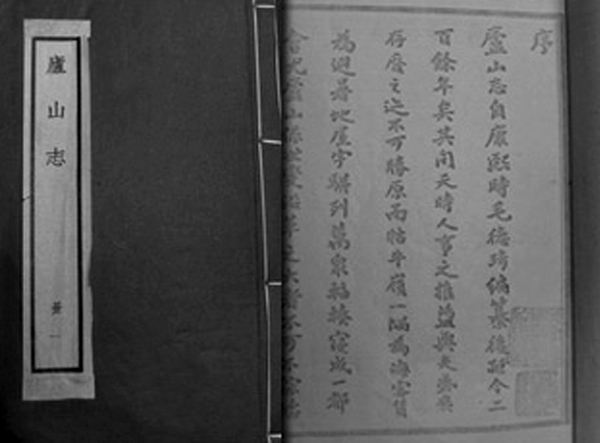
《庐山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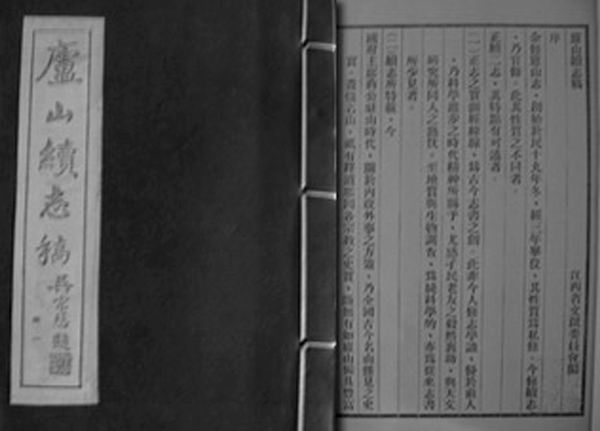
《庐山续志稿》
吴宗慈(1879-1951),字蔼林,江西南丰人,他的头衔叫“方志学家”。与朱熹一样,人们多是通过志书来了解一地,志书具体到一座座山,便是山志。在山读志,不仅是亲切的应景,更让人真正读懂山林独具的卓然个性与品格,生无限灵感幽情。有吴宗慈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是庐山之福,更是后人之福。
作为古来名山之一,庐山并不乏志书,从东晋慧远和尚开始,历代皆有撰者。吴氏志书之前,较精的有明代桑乔曾所撰《庐山纪事》十二卷,康熙年间吴炜“继为编辑”,增补了清代部分史事。可惜的是,刻成不久,板毁于火,因而流传不广,其后星子县令毛德琦又依照桑、吴刻本重订。毛编资料广泛详实,流传最广。胡适1928年写《庐山游记》时,依据的便是上述三种山志。但最晚出的毛编也只截至清代,不足以涵盖近代中国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波涛汹涌。
吴宗慈《庐山志》的可贵之处,正在详尽叙写了庐山的近代历史,在书中这部分叫做“山政”。中国上古时代的全国性方志《尚书》,分为方域、山川、土质、物产、贡赋等五章来记述天下四方之事,后来的志书名目逐步增至疆域沿革、风俗、物产、城镇、人物、名胜、古迹和艺文等,庐山旧方志也大体沿袭此例。吴宗慈的《庐山志》分为七部分:地域、山川胜迹、山政、物产、人物、艺文、杂识。其中“山政”古所无有,为吴宗慈新创。按理说,一座中国境内的山谈不上什么“政治”,但因为适合避暑的自然条件和靠近传教士云集、而一到夏天闷热无比的武汉、上海等地,庐山偏偏“牯牛岭一隅为海客赁为避暑地,屋宇骈列,万众辐辏,?成一都会,尤庐山系世变沿革之大者”,成为我国唯一被列强辟为租借地的山林,并因此经历了地方政治权力的变更――1885年一位名叫李德立的英国传教士看中庐山牯牛岭的东谷后,通过赠送礼物、借用当地士绅为中间人等多种手段得到经营约四千五百亩山地的永久租约。李德立是个天才的地产策划人,他取汉语牯牛岭和英语“COOLING”(清凉)的共同谐音将之称为牯岭,英文名“KULING”。精心规划之后,李德立修建起一系列符合西方生活娱乐习惯的公共设施,将地皮按面积划成小片,在报纸上大做广告编号售出。1895年由英国驻浔领事雷夏伯与浔阳道台双方签字,李德立占有长冲一带土地的租借权,时间长达999年,每年交租金十二千文银――基本等同于无。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接踵而至,以各种方式分占庐山以为租借地。1896年,庐山英租借地界成立大英执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七名英国传教士加两名美国传教士成为委员,主席李德立。洋人们以租界的方式管理牯岭,自行设置了巡警,维持公安,中国官方不能过问山上租地内的事宜。直到1927年,外交部特派驻九江交涉员林祖烈认为牯岭属于洋人私人租借,并非租界,于是牯岭被称为特区,中国官方收回警察行政权。但直到1936年1月1日,庐山主权才被收回。
庐山遭遇了近代中国的独特因缘。据1930年庐山管理局调查统计,仅英国人租借的牯岭特别区就有房屋526栋,到1931年,居民共来自18个国家,被胡适认为“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山政”一纲,详叙了山上各租借地诸交涉案。
在近代中国的飘摇岁月里,庐山迎送着一批批中西山客,人们集中居住在这块小小山地,在各自的世界中忙碌,将庐山绘制成一幅中西、新旧交错的政治文化图景。蒋介石来了,忙着布置新的“剿匪”计划,依照德国将军赛克特的建议用中西结合的军队文化训练军官25000余人,庐山的主要街道牯岭街常有他和夫人宋美龄视察新生活运动的影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了,他在黄龙寺后的鹿野山房半隐居,建桥立椅,刻下“同胞请坐,有姨太太的不许坐”的幽默;秦仁昌、胡先?与陈封怀来了,经营刚创办的庐山植物园,忙着标本与资料收集;张之洞的高足李拙翁来了,他偶尔看见一块题有“花径”的石头,考证为白居易手迹,缘此重建“花径”与景白亭;牯岭美国学堂的孩子们度过了有童子军、化妆舞会、音乐会等各式活动的童年,学堂校长罗伊・奥尔古德在五老峰留下一座供后人避雨的“待晴亭”,留下庐山上唯一一块英文石碑。
这时,离李德立最初来到庐山已经三十多年过去。这块他只想作为世外桃源的清凉山地在中西文化的交错中演变为如此丰富独特的文化载体,该是李氏始料不及的。其中多少沧桑,多少故事散在庐山的一石一木间,无人捡拾。
幸有吴宗慈
那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偶尔的,吴宗慈会去万松林中的松门别墅拜望客居山中的文化老人陈三立。万松林正是1898年冬天卜居此间的庐山开发者李德立所植。李德立爱赏中国意境,在居处四周的山谷中遍植青松,以成清幽。在松门别墅中,吴宗慈与老人闲散地聊着天,窗外或风和日丽,或山雨滂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处处成荫的松涛中,他们很自然地聊到李德立,聊到他最初想租山下九峰寺,结果价格没谈好,被原是湘军兵弁的方丈继慈和尚一怒之下打了出来的趣事;聊到德化知县认为姓李名德立自然是中国人,就允了他买地之请,待到见面,才发觉这种名姓也有可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聊到在海外轮船上贴的牯岭公司的巨大广告,聊到李德立不雇佣庐山山民,招致愤怒,差点被众人打死;他们也聊到各国的人们为了租地想出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措辞,聊到庐山新增出的国民政府要人题的石刻等。陈三立还聊到自己光绪十九年在庐山做的诗,那时,他法六朝汉魏,与晚年诗风迥然不同,这些诗也散佚了。后来,他们聊到山志,便有叹息,才过去三十多年,连历史上变化最大的牯岭避暑地租借给外国人的本事记得的人就已少见,那么后代呢?后代在面对这片山水的时候,还能记得几许风烟掩盖下的始末?他们赖以认识这座山的,难道还只能是前人古志?可那里面描述的,是还没有成为山林城市的庐山啊――看来山志真应该重修了。
厚厚的《庐山志》,一切的起因,来自那日陈三立与吴宗慈交谈时叹息中的惧怕,惧怕一段山的历史不能够被人记得,从此丢失在沧桑里。《庐山志》修竣后,确实保留了许多李德立开发牯牛岭的历史细节,使这些旧事遗闻未随故老远去。尤值一提的是志书中山里摩崖金石文字的第一手资料,已经无法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中,许多石刻如李北海书复东林寺碑、九十九盘路南岭的王阳明书庐山高三字等在硝烟中消失殆尽,只有在吴氏《庐山志》中觅其旧影。同时,吴宗慈在《庐山志・副刊》中还保存了26题30首陈三立光绪十九年的庐山纪游诗,为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所失收,成为迄今能见到的陈三立最早作品,对研究陈三立诗歌的近代文学学者颇有助益。
在陈三立的鼓励下,吴宗慈接受了编写山志的任务。募捐筹款之外,他的修志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去庐山南北麓履勘咨访,“穷探博采,目验心解,所获甚夥”。他到深山中寻访详知攻击李德立事的老人,倚靠药农的帮助凌绝顶以探摩崖文字。第二步是“援据群籍,购求秘本,孜孜铅椠,昕夕不辍”,以实地考察的经验为基础,多方搜集购求与庐山有关的方志、别集、笔记、诗词,以做到言出有据。这两个过程耗费了巨大的精神气力,吴宗慈那时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从不假手他人,事无巨细艰易,一身兼之。
最后一步是落笔成文。吴宗慈注重使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来解释庐山现象,邀请各学科专才共同参与山志的编纂。陈三立称赞他“侈特创,既佐以图表,复参以后起专门新技术,务在纠缺误,辟归于详实而资利用”。新体例与旧体例、新文体与旧文体在吴宗慈看来并不矛盾,而是相应相生,正是“旧从其旧,新从其新”的指导思想,成就了《庐山志》中最漂亮的李四光所作《地质志》和胡先?所作《植物目》。两者都是可以独自成篇、专业知识与文辞俱美的佳作。李四光根据对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考察,在论文《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川》和专著《冰期之庐山》的基础上,将“第四纪冰期说”作为解释庐山地貌的基础。胡先?是中国近代植物学奠基人之一,他以前沿的植物学知识为庐山物产分类命名,如根据庐山“云锦花”的植物习性,将其定名为“云锦杜鹃”载入植物学名册。才四年的时间,一本七纲十二卷三十目精巧工细的山志便付印了。当初人们捐助修志的钱财还有余款,用这些余款在铁船峰上修建了一座静观亭,山林由此又多了一份景致。较之如今的许多文化工程,这“斯作亦可空前矣”的民间作为,可谓轻捷。
《庐山续志》的编纂也是来自于这份对记忆丢失的惧怕。1939年4月庐山沦陷,被日军侵占了6年之久。这是庐山山史上的空前文化浩劫,战后成立的庐山管理局限于能力,只能对损毁的建筑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修缮。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也就是吴宗慈编写《庐山志》12年后,为编纂《庐山续志》,他重到庐山,又重新开始收集整理史料。那时,陈三立已然仙逝,吴宗慈也自称“天涯倦鸟”,但庐山令他感到“峰峦识我迎微笑,泉石依人作旧妍”的兴奋,更感到这片山水对他“新材待访续前编”的期望。支持着他的,依然是对乡邦文化丢失的惧意。1947年6月,《庐山续志》全书脱稿,在《续志》中吴宗慈详细记载了日军对庐山轰炸造成的古寺庙建筑、名人别墅、地表生态、馆藏文物的损毁情况,如归宗寺三国吴赤乌时所建舍利山铁塔等被毁;庐山植物园被日人运走的160箱标本、图书,战后经政府于1946年春向日本交涉追回80%,然而名贵植物种类标本无一返回。值得一提的是,利用同时代人的便利,吴宗慈在《庐山续志稿》中为林森和蒋介石撰写了从1932年6月开始的庐山“起居注”。今天看来这部分有些异样,但毕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想法,按照想法去做了,留给历史的便是一份记录。
“从来无限沧桑事,都付山僧一枕眠”,吴宗慈在庐山写的这两句诗透着世事洞明的潇洒。1935年《庐山志》修竣后,吴宗慈将修志时所搜集的一大批书籍全部捐献给庐山图书馆,以滋养后人。
有人将历史研究工作分成三种活计,一种人是规划师,规划出美好的理论蓝图,一种人使用砖瓦,搭建出华丽的房屋,还有一种人,尽心尽力地做着砖块,力图将它们做得更坚固厚实。有能力做房屋的,特别是有规划天才的人,自然令人仰望,油然而生崇敬;对于做砖块的人们,这敬意便带了几分肃然。
陈三立称赞吴宗慈为“精勤”,这两字送给吴宗慈不为过褒。文字,或许不应只限职业,更应禀据保存文明的惧怕与天性中对文化的浓情,“慨然以为己任”,才能真正做到“精勤”。对于利用志书的人们,善于借其探寻中华文明的千年精髓,才是理解了这份惧怕与浓情。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江西财经大学讲师
(本文编辑 乔向春)
